当微风掠过氟化工园区的角落,一簇淡粉色的小花悄悄舒展着花瓣。它是月见草,细长的茎秆顶着几片锯齿边的绿叶,根须深深地扎进脚下的土壤。它的个头不高,花期很短,但是它不挑环境,耐旱、耐寒,哪怕在污染较重的土壤中,也能抽出新芽、开出小花。 月见草的这种看似柔弱实际却坚韧的生命力,恰恰是西湖大学张岩岩实验室团队眼中珍贵的品质——一朵小花中或许藏着破解“永久性化学品污染”的线索。
野外生长的月见草。 “它是PFAS污染环境中的winner”张岩岩团队长期深耕全氟化合物(PFAS)分析检测和降解治理研究。这类被称为“永久性化学品”的物质,凭借稳固的碳—氟键结构,具备极强的抗降解性,广泛应用于众多领域——不粘锅涂层、消防泡沫、冲锋衣防水面料、电镀涂层甚至半导体芯片中都有其身影。 PFAS的稳定性在为工业制造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却也持续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给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威胁。但由于其优异的稳定性能目前还难以被其他化学品取代,因此尚无法彻底禁用。 张岩岩团队来到中国东部某个有着60年排放史的氟化工基地开展研究,初衷很简单:采集水样,分析里面的PFAS成分,探寻降解的方法。 在这一过程中,深耕生物质基材料构建与全生命周期评价的王蕾研究员,也希望通过利用储量丰富的生物质资源构建富集材料,为PFAS去除贡献一份力量。 这时候,有着土壤重金属植物修复研究经验的郭心雨博士出现了。依托西湖大学浙江省海岸带环境与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平台,郭心雨成为张岩岩和王蕾研究员联合培养的博士后。 郭心雨介绍,重金属土壤修复中,有一种成熟的修复手段叫做超积累植物,指的是植物能吸收利用并积累耐受环境中的污染物,将它们输送并贮存在植物体的地上部分,从而降低土壤污染,达到修复目的。“重金属超积累植物大部分都是从长期污染的场地中发现或筛选出来的,是环境胁迫下自然进化的结果。”郭心雨说。 “长期受PFAS污染的土壤”“植物修复”“环境驯化”“生物质利用”,这些关键词碰撞下,一个问题诞生了——或许从氟化工周边,也能筛选出对PFAS积累能力高的植物? 这个想法像一颗种子,迅速生根发芽。有交叉学科背景支撑,再加上现成的污染场地,大家一拍即合,立刻启动了实验计划。她们选了8种植物,4种草本、4种木本,小心翼翼地采集根、茎、叶,甚至木本植物的树皮,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检测结果显示,木本植物对PFAS的积累能力普遍偏弱,4种草本植物里,一枝黄花虽有潜力,却因入侵植物的身份被排除。唯有月见草,交出了一份惊艳的答卷——对18种PFAS的叶片积累因子(LCF)大于10,转运因子(TF)大于3。 “这两个数字,就是超积累植物的‘身份证’。”郭心雨介绍,“LCF大于10,说明它的叶子能牢牢‘抓’住PFAS;TF大于3,意味着它能把根吸收的污染物,高效转运到茎叶上。”对植物修复来说,这两点至关重要——只有污染物集中在地上部分,后续收割才能真正带走污染。 为了摸清月见草的“过人之处”,团队特意从无污染的背景区域找了同种月见草做对比。实验室水培结果显示:污染区月见草对PFAS的转运因子是背景区的15倍。深入研究后,谜底终于揭开,关键就在植物根系的细胞壁上。 细胞壁是污染物进入植物体内的第一道屏障,其主要组分——果胶和半纤维素可以结合大量污染物。背景区的月见草遇到PFAS,会立刻启动防御,拼命增加果胶和半纤维素的含量,把污染物牢牢锁在根部;在污染区“驯化”多年的月见草,却早已学会“以柔克刚”——它的细胞壁成分几乎没变化,减少了对PFAS的结合,让更多污染物顺利转运到茎叶。 “可以说月见草是高浓度PFAS污染环境当中的winner。”郭心雨的语气里满是敬佩,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中,它不仅没被PFAS毒害,还练就了积累污染物的超能力。 为了避免野外采样的不确定性,研究团队进行了实验室复现:污染区采集的月见草对该场地最主要的PFAS——全氟辛酸(PFOA)的转运因子为4.67,实验室水培的样本也达到了3.71,且在较高污染浓度的土培实验中其转运因子依然保持在3以上,月见草对PFAS的超积累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郭心雨在做实验。 这株在荒径中默默生长的月见草,就这样意外地走进了科研视野,用它柔弱的身躯,“扛”起了治理PFAS污染的重任。 以自然之道还治自然找到月见草这把“钥匙”,只是治污之路的第一步。张岩岩团队很清楚,科研不能只停留在实验室里,如果将收割后的月见草随意处置,PFAS会重新回到环境中,这也意味着所有努力都白费。 这份清醒,让团队早早确立了必须评估治理技术可持续性的理念,也因此与在全生命周期评价领域拥有多年经验的王蕾研究员建立了早期合作。 不仅要让植物吸收污染,还要给这些“污染载体”找一个安全的归宿。她们把目光投向了热解技术,这是一种能让污染物彻底分解的处置方式。 热解的过程很奇妙:将收割后的月见草放入高温设备,在500摄氏度的条件下,植物体内的PFAS会被彻底分解,去除率高达99.2%。更令人惊喜的是,热解后产生的生物炭,经检测完全符合国家低质煤标准,既能安全利用,还能实现能量回补。 要知道,传统的高温焚烧技术需要直接处理污染土壤,能耗巨大;化学洗脱法则要添加大量试剂,会破坏土壤肥力和生物活性。全生命周期评价显示,与传统治理技术相比,来自月见草的这套方案的碳排放和能耗都是负值。 简单来说,不仅没有给环境添负担,还通过生物炭的利用回补了能量。 “月见草这个植物本身就是自然的一员,我们的修复方法其实是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郭心雨解释道。 团队并没有停下脚步。在张岩岩看来,月见草也像研究的树干,在这个基础上,还能生长更多的分支。 她们相信,月见草的积累转运能力还能提升——比如通过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的方式,进一步提高植物的修复效率。郭心雨还在尝试水热技术,希望能找到比热解更绿色、更低能耗的末端处置方式。 团队还发现,月见草对不同PFAS的积累转运能力差异较大,这与PFAS的分子质量有关,也与其在污染区域的浓度有关。例如,月见草对PFOA的替代品、污染严重的六氟环氧丙烷三聚体酸(HFPO-TrA),转运因子高达5.76。而对备受关注的另一类PFAS——质量相当的全氟辛基磺酸(PFOS),转运因子仅有2.46。这是由于该污染区域位于氟聚物生产企业附近,PFOA和HFPO-TrA均为其生产助剂,土壤浓度是PFOS的上百倍。 这表明,超积累植物的修复能力依赖于其“原生”环境的污染物组成,并不是解决所有PFAS污染的一把“万能钥匙”。 “比如说另外一个地方,可能会筛选出另一种对特定PFAS具有更好修复效果的超积累植物,从科学逻辑上来说,这是可预期的。”张岩岩说。 从月见草修复污染土壤,到热解处置产生生物炭,再到生物炭资源化利用,一条完整的绿色治理闭环就此形成。这朵小小的月见草,不仅自己成了治污“高手”,或许能在未来带动一整套绿色治理方案的诞生。 5年,新污染物治理迎来发展春潮 张岩岩至今记得,5年前刚从海外回国时,跟企业聊起PFAS,对方大多一脸茫然:“这是什么东西?跟我们有关系吗?”那时,新污染物治理还停留在少数科研者的视野里,政策支持、产业关注都远远不够。 “十四五”这5年,是张岩岩团队深耕PFAS治理的5年,更是我国新污染物治理领域飞速发展的5年。2022年,国务院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引发了全社会对新污染物的关注。 “变化非常明显。”张岩岩说。现在,新污染物治理成了共识。 一开始,她接到来自管理部门、企业的邀请,是去开讲座、做培训,讲解PFAS的危害和治理思路。到如今,邀约从科普走向实际应用——与管理部门和企业合作开展治理技术的中试应用,为污染治理提供可推广方案,为排放标准制定提供技术保障。 从2022年11月生态环境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到我国各省级行政单位均制定了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从六大重点行业涉新污染物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一步加强,到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新污染物治理纳入推动全面绿色转型的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政策的春风,让科研工作如虎添翼。 在刚刚结束的浙江省新污染物治理年会上,张岩岩听到了很多务实的讨论:重污染场地该用什么技术,轻度污染场地该如何布局,如何平衡治理成本和效果。管理部门的清晰规划,让科研团队的方向更明确——她们的月见草修复技术,也是未来适配污染源已切断、面积广、不急需复用的中轻度污染区域的绿色选择之一。 “植物修复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也需要树立分类处置的思路。”张岩岩解释说,对于那些重污染、修复时间紧张的场地则适宜探索更加“短平快”的技术。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 新污染物治理是一项长期任务,如何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如何完善不同行业的治理标准,如何让更多像月见草这样的“治污高手”被发现,都是摆在科研者面前的课题。 “PFAS是很多工业领域的关键化学品,从生产源头进行污染治理和绿色替代,促进产业绿色转型,才是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路。”张岩岩说。 这五年,张岩岩见证了新污染物治理从“鲜有人知”到“社会关注”的转变,也亲历了从“技术探索”到“方案成型”的突破。 在她看来,月见草的发现,不仅是一项技术成果,更传递了一种治理理念——自然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在等待我们发现。 正如张岩岩所说:“真正有价值的科研,既要扎根实验室追求真理,更要立足现实解决问题。”
实验采样地点。 粉瓣藏锋,草木含章。小小的月见草,不仅破解了污染难题,更见证了漫长而艰辛的科研路上,科研者的坚守与时代的进步。 可预见的是,在新污染物治理的春潮中,会有越来越多的科技支撑,汇聚成守护生态环境的磅礴力量。
链接:相关成果以《Identification of a PFAS hyperaccumulator and elucidation of its translocation mechanism for sustainable phytoremediation》为题发表于国际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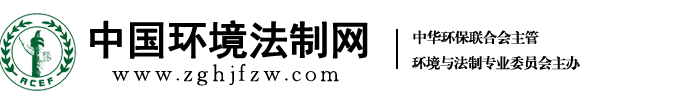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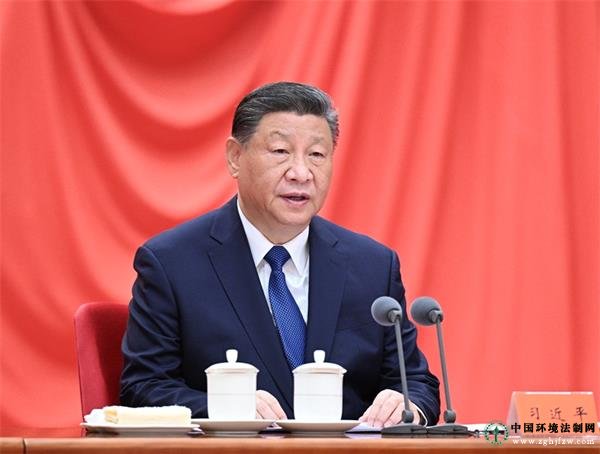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6702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6702号
